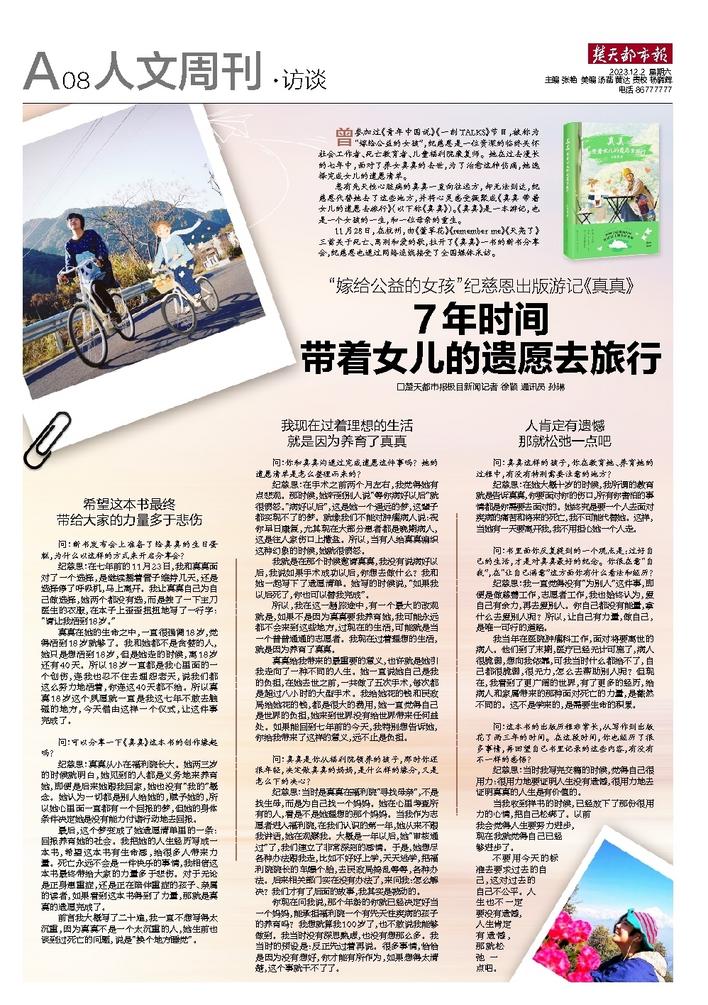□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通讯员 孙琳
曾参加过《青年中国说》《一刻TALKS》节目,被称为“嫁给公益的女孩”,纪慈恩是一位资深的临终关怀社会工作者、死亡教育者、儿童福利院康复师。她在过去漫长的七年中,面对了养女真真的去世,为了治愈这种伤痛,她选择完成女儿的遗愿清单。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真真一直向往远方,却无法到达,纪慈恩代替她去了这些地方,并将心灵感受凝聚成《真真 带着女儿的遗愿去旅行》(以下称《真真》)。《真真》是一本游记,也是一个女孩的一生,和一位母亲的重生。
11月28日,在杭州,由《萱草花》《remember me》《天亮了》三首关于死亡、离别和爱的歌,拉开了《真真》一书的新书分享会,纪慈恩也通过网络连线接受了全国媒体采访。
希望这本书最终
带给大家的力量多于悲伤
问:新书发布会上准备了给真真的生日蛋糕,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启分享会?
纪慈恩:在七年前的11月23日,我和真真面对了一个选择,是继续插着管子维持几天,还是选择停了呼吸机,马上离开。我让真真自己为自己做选择,她两个都没有选,而是拽了一下主刀医生的衣服,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请让我活到18岁。”
真真在她的生命之中,一直很强调18岁,觉得活到18岁就够了。我和她都不是贪婪的人,她只是想活到18岁,但是她走的时候,离18岁还有40天。所以18岁一直都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创伤,连我也忍不住去埋怨老天,说我们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连这40天都不给。所以真真18岁这个夙愿就一直是我这七年不敢去触碰的地方,今天借由这样一个仪式,让这件事完成了。
问:可以分享一下《真真》这本书的创作缘起吗?
纪慈恩:真真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她两三岁的时候就明白,她见到的人都是义务地来养育她,即便是后来她跟我回家,她也没有“我的”概念。她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给她的,赋予她的,所以她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回报的梦,但她的身体条件决定她是没有能力付诸行动地去回报。
最后,这个梦变成了她遗愿清单里的一条:回报养育她的社会。我把她的人生经历写成一本书,希望这本书有生命感,给很多人带来力量。死亡永远不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相信这本书最终带给大家的力量多于悲伤。对于无论是正身患重症,还是正在陪伴重症的孩子、亲属的读者,如果看到这本书得到了力量,那就是真真的遗愿完成了。
前言我大概写了二十遍,我一直不想写得太沉重,因为真真不是一个太沉重的人,她生前也谈到过死亡的问题,说是“换个地方睡觉”。
我现在过着理想的生活
就是因为养育了真真
问:你和真真沟通过完成遗愿这件事吗?她的遗愿清单是怎么整理而来的?
纪慈恩:在手术之前两个月左右,我觉得她有点悲观。那时候,她听到别人说“等你病好以后”就很愤怒。“病好以后”,这是她一个遥远的梦,这辈子都实现不了的梦。就像我们不能对肿瘤病人说:祝你早日康复,尤其现在大部分患者都是晚期病人,这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所以,当有人给真真编织这种幻象的时候,她就很愤怒。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邀请真真,我没有说病好以后,我说如果手术成功以后,你想去做什么?我和她一起写下了遗愿清单。她写的时候说,“如果我以后死了,你也可以替我完成”。
所以,我在这一趟旅途中,有一个最大的改观就是,如果不是因为真真要我养育她,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来到这些地方,过现在的生活,可能就是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我现在过着理想的生活,就是因为养育了真真。
真真给我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就是她引我走向了一种不同的人生。她一直说她自己是我的负担,在她去世之前,一共做了五次手术,每次都是超过八小时的大型手术。我给她花的钱和民政局给她花的钱,都是很大的费用,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的负担,她来到世界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益处。如果能回到七年前的今天,我特别想告诉她,你给我带来了这样的意义,远不止是负担。
问:真真是你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那时你还很年轻,决定做真真的妈妈,是什么样的缘分,又是怎么下的决心?
纪慈恩:当时是真真在福利院“寻找母亲”,不是找生母,而是为自己找一个妈妈。她在心里考查所有的人,看是不是她理想的那个妈妈。当我作为志愿者进入福利院,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她从来不跟我讲话,她在观察我。大概是一年以后,她“审核通过”了,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刻的感情。于是,她想尽各种办法跟我走,比如不好好上学,天天逃学,把福利院院长的车爆个胎,去民政局捣乱等等,各种办法。后来相关部门实在没有办法了,来问我:怎么解决?我们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其实是被动的。
你现在问我说,那个年龄的你就已经决定好当一个妈妈,能承担福利院一个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的养育吗?我想就算我100岁了,也不敢说我能够做到。我当时没有深思熟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的预设是:反正先过着再说。很多事情,恰恰是因为没有想好,你才能有所作为,如果想得太清楚,这个事就干不了了。
人肯定有遗憾
那就松弛一点吧
问:真真这样的孩子,你在教育她、养育她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纪慈恩:在她大概十岁的时候,我所谓的教育就是告诉真真,你要面对你的伤口,所有你害怕的事情都是你需要去面对的。她终究是要一个人去面对疾病的痛苦和将来的死亡,我不可能代替她。这样,当她有一天要离开我,我不用担心她一个人走。
问:书里面你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对真真最好的纪念。你很在意“自我”,在“让自己满意”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和经历?
纪慈恩:我一直觉得没有“为别人”这件事,即便是做慈善工作,志愿者工作,我也始终认为,爱自己有余力,再去爱别人。你自己都没有能量,拿什么去爱别人呢?所以,让自己有力量,做自己,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我当年在医院肿瘤科工作,面对将要离世的病人。他们到了末期,医疗已经无计可施了,病人很脆弱,想向我依靠,可我当时什么都给不了,自己都很脆弱,很无力,怎么去帮助别人呢?但现在,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有了更多的经历,给病人和家属带来的那种面对死亡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这不是学来的,是需要生命的积累。
问:这本书的出版历程非常长,从写作到出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你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再回望自己书里记录的这些内容,有没有不一样的感悟?
纪慈恩:当时我写完交稿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用力:很用力地要证明人生没有遗憾,很用力地去证明真真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当我收到样书的时候,已经放下了那份很用力的心情,把自己松绑了。以前我会觉得人生要努力进步,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够进步了。
不要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过去的自己,这对过去的自己不公平。人生也不一定要没有遗憾,人生肯定有遗憾,那就松弛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