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迅,文学博士,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武汉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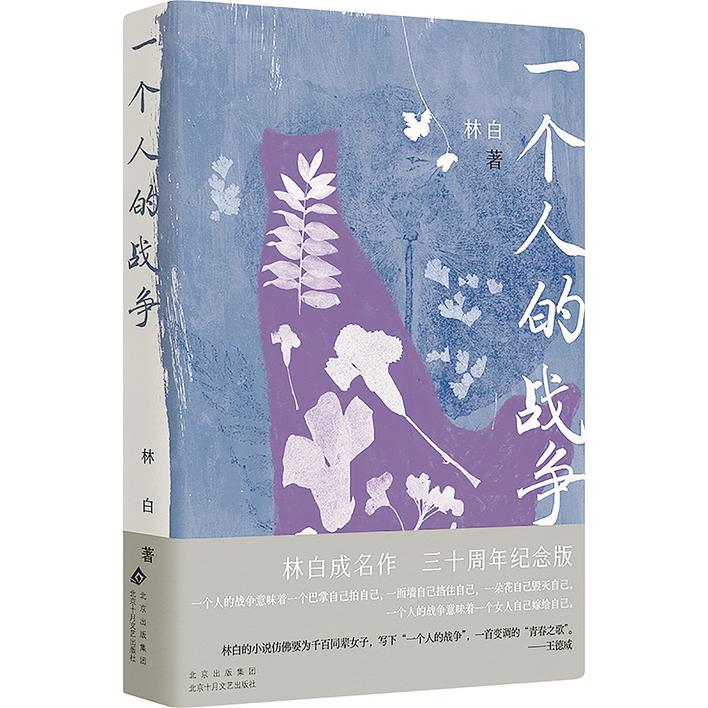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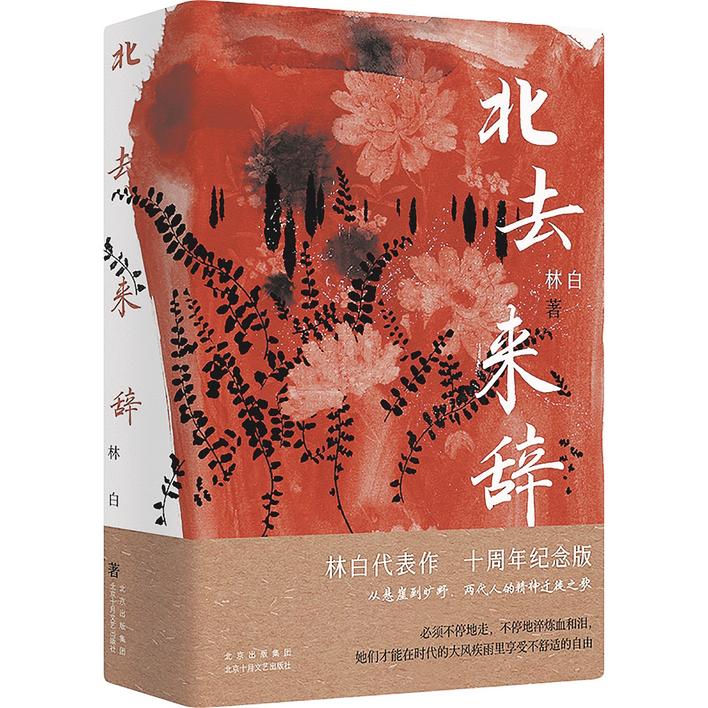
□徐迅
2025年初,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林白的三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北去来辞》,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女性三部曲”为题重新出版发行。之所以组成“女性三部曲”,是因为林白将这三部作品视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代表,是她个人用文字对女性生命体验所做的深刻探索。《一个人的战争》最初于1994年发表于《花城》杂志,迄今已有三十年,“女性三部曲”也是林白用三十年时光构建起的小说世界。
对女性“成长”主题的关切和言说贯穿了林白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写作,三部小说构成了女性成长“三部曲”,是女性不同阶段的个人成长史,是“一个女人的史诗”。
《一个人的战争》:用飞翔之姿超越现实
《一个人的战争》以女性成长为主题和线索,呈现的是少女林多米的成长。
作品是林白带有自传性的小说,讲述来自边陲小镇B镇的林多米幼年失父,母亲常年不在家,幼小的她除了孤独,内心充满了对情感的强烈渴求。
青年林多米的生活大起大落、富有戏剧性和文艺气质,发表诗歌、考上大学、漫游大西南、撕心裂肺的“傻瓜爱情”、逃离故土……她对日常生活是不满的,常常耽于幻想、白日梦中,在电影、梦境里逃避现实。小说中,林白有意用诗意涂抹“日常生活”,让梦想的飞翔超越现实。小说中那些大胆而唯美、隐晦且充满神秘感的女性身体的书写,一度受到评论界广泛的关注和褒扬。当林白的小说创作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日渐走向成熟时,她以独特的个人化写作姿态,对女性成长、心理、命运、地位的思考和探索则显得更为深切,林白也成为“女性写作”和“个人化写作”的一面旗帜。
林白坚守女性立场,关注女性命运,塑造了许多不同于男性文化想象的真实的女性形象。
《说吧,房间》:“以血代墨”的书写
《说吧,房间》在《花城》杂志发表时,主人公还叫“老黑”,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的作家修订后的《说吧,房间》单行本里及之后,主人公改成了“林多米”,与《一个人的战争》中的主人公名字一致,这表现了作者早有构建“三部曲”的意图。
《说吧,房间》用“以血代墨”的方式,表现初为人妻和人母的林多米对婚姻家庭生活和女性身份巨大转变的深切体悟与切肤之痛。其中一个重要元素是表现女性独有的流产、怀孕、生育、哺乳、节育等生理体验和生命经历,这也是作品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特征与生命状态,从青春期开始,女性的生命史就是用鲜血与疼痛写就的一部个人历史。
《说吧,房间》有着大量的对女性生活日常具体的书写,展示了女性所经受的肉体磨难与精神痛苦,揭开了男性书写对这一过程的遮蔽,让人看到女性蒙受的生育苦难。与男作家不一样,带着女性的敏锐与细腻,林白笔下的人物凸显出强烈的女性生命意识与性别意识。
林多米像大多数职业女性一样,在工作和家庭中一人分饰两角,在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两个角色间不停地来回切换。白天在公交车里挤成照片人一样上下班,在单位参与社会竞争,在工作中要和男性一样承担责任;回家后又要完成一个贤妻良母的义务,生育和抚养孩子,操持家务。多米在一种无穷无尽的重复性劳动中消耗生命,自己写作的梦想早已渐行渐远,连好好睡上一觉都成为奢望。在繁重的工作和琐碎的家务的双重压力下,疲惫不堪。离婚又直接让她在单位的分流中被解聘。为了生存,到处求职,一个临近中年的下岗女人的求职路上尽是心酸,多米幻想着自己和女儿变成了老鼠。三次求职均以失败告终,尝遍了辛酸、绝望和悲凉,最后在黑夜里面对自己哭泣。
《说吧,房间》尖锐揭示了部分当代女性的境况: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看似是独立的多米们,也会遭遇到“女性”的生活困境。
《北去来辞》:自我审视与沉入民间
《北去来辞》主人公虽起名为海红而不是林多米,但是在这部明显带有半自传体色彩的小说里,主人公海红和林多米一样,都是大学毕业后孤身一人在省图书馆、电影制片厂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热爱写诗和做白日梦,在一次短暂婚史后嫁给了北京的一位老人,逃离了原来的生活,并且来到北京后经历了生育、下岗等人生大事,这些情节与事件与《一个人的战争》和与《说吧,房间》有一定重合。
《北去来辞》的上部对海红童年与青年时的成长过程,以及在北京生育、下岗的经历全部讲述完毕,下部讲述的是海红与道良离婚、与瞿湛洋的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工作,出于内心“亲情”的召唤回归到道良身边,最后来到银禾家乡农村的乡野大地劳动耕作、回到故乡圭宁的见闻等人生经历,夹杂着五十岁的海红对爱情婚姻、自我成长、城市与乡村等更为深刻、成熟的认识。
海红的故事是一个女人“在路上”的成长故事,是青春远去、步入中年的作家,在“文字知天命”的叙述下,告别幻想、崇尚实际、自我审视、沉入民间大地的一种“中年情怀”;是少女和青年的林多米成为海红后,通过自我积累和自我调整,认识自身而后认识世界的心灵成长史。
女性成长:揭秘女性生存与内心世界
林白一直钟情于女性成长主题,在小说人物身上倾注自己的经验。
关注女性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女性转变为成熟母亲和成熟女人后,在心理各方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中女性书写的一个空白。
学者戴锦华指出,文学中对女性成长的书写大多集中在少女阶段,包括外国经典小说《简爱》,故事结尾在“我嫁给了他”之后便戛然而止;新时期文学初年的女性书写中,也是“滞留的少女”。“关于女性成长的叙述,不仅缺少与男性成长故事相对应的明确段落,而且事实上呈现为一些无法彼此相衔的、破碎的段落”。
正如西蒙·波伏瓦所说,整部妇女史是由男人写就的。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表述和文学叙事中,对少女成长为女人的变化是隔膜的。“少女已成为一位成熟的、充满母爱的母亲,或形形色色的病态的‘成熟’女性,无人知晓或曰无人关注,在这落下的帷幕背后,那永恒的美丽少女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和成长;这变化与成长无疑联系着一个生理过程,却显然有着更多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
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更是类型化、扁平化的,大都处在某种静止状态之中。女性从少女阶段,到少妇、母亲,步入中年、老年,都是成长。从一个女孩到一个母亲是绝大多数女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其间伴随着生理与心理上的变化,必然涉及成为母亲后的生命经验和身体体验、在哺乳期身体的变化与哺乳的感觉、身为人母的快乐与抚养孩子的压力、遭遇工作危机和家庭生活双重狙击时的人生困境、不断发生的爱与痛、内心的彷徨与焦虑、身体的疲惫与憔悴、化蛹成蝶的蜕变、岁月沉淀与经历渐长中的日趋成熟圆润,等等。
林白的“女性三部曲”揭秘女性生存与内心世界,表现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成长,既有生理层面的,也有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脉络清晰,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作品中,从超现实主义年轻女诗人林多米到成长为“知天命”的海红,人物从耽于梦想归于日常,从激烈对抗趋于和解;而作家林白,则从年轻时的“飞翔之姿”到中年的“文字知天命”,从“以血代墨”的激情到“风雨同行”的自洽,带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以丰沛的创作写就了另一部“女性的史诗”。